真正的某某某早已被抽干脊髓液出自哪
粉丝2.1万获赞211.3万
相关视频
 01:2452青柠柠
01:2452青柠柠 05:33查看AI文稿AI文稿
05:33查看AI文稿AI文稿小朋友,来吃颗糖!这句慈祥的话语,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都伴随着一颗白色小糖丸的甜蜜记忆。 然而,很少人知道,这枚小小糖丸背后承载着一位医学家一生的心血,以及中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壮举。 这位被誉为唐皖爷爷的顾方舟,用一生守护了亿万儿童的健康。一九五五年, 中国南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脊椎灰质炎疫情,短短时间内,一千六百八十人感染,四百六十六人死亡。病毒迅速蔓延至青岛、上海等地, 所到之处,无数儿童瘫痪甚至丧命。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年轻病毒学家顾方舟接到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研制中国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当时,美国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已经研制出注射用灭活疫苗,但成本高昂,每季高达五美元,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承受的。另一种由阿尔伯特萨宾研发的口服碘毒活疫苗尚在试验阶段,前景未卜。面对技术封锁和资源匮乏, 三十一岁的顾方舟毅然接下了这个关乎民族未来的重担。一九五九年, 顾方舟带领团队来到昆明郊外的玉案山,这里将成为中国脊椎灰质炎疫苗的摇篮。迎接它们的是荒山野岭和简陋的猴子饲养房。因为疫苗研发需要大量灵长类动物进行实验, 他们住的是自己搭的草棚,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的团队从零开始建起了实验室和疫苗生产基地,最困难时,连实验用的猴子都吃不饱, 研究人员只能省下自己的口粮喂养它们。一九六零年,疫苗初步研制成功,但谁来做第一个临床试验者?面对可能致残甚至致命的未知风险,顾方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是负责人,我来世。 他毫不犹豫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后,他依然健康,但这还不够,成人对脊椎灰质炎病毒大多有免疫力, 真正的风险在于儿童。于是,一个更艰难的决定摆在了面前,需要儿童志愿者。顾方舟抱起了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如果不敢给自己的孩子吃,凭什么给全国人民的孩子吃?这个决定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 特别是他同样身为医学研究员的妻子李怡婉。最终,在顾方舟的坚持下,包括他儿子在内的首批儿童服用了疫苗。在接下来漫长的观察期里, 顾方舟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他后来坦言,那些日子,我每天看着儿子,心里像悬着一块石头。 当所有孩子都安然无恙的消息传来时,这位坚强的科学家第一次在同事面前流下了眼泪。 疫苗虽然成功,但推广又遇难题。液体疫苗需要冷冻保存,当时中国大多数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 顾方舟再次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他将液体疫苗融入糖丸中,创造出了中国孩子都熟悉的糖丸疫苗。这不仅仅解决了保存和运输问题,更消除了孩子们对打针的恐惧。 一颗小小的糖丸,既是科学的结晶,也蕴含了对儿童的深切关爱。一九六二年,糖丸开始在全国推广,发病率随即直线下降。到了一九九零年, 中国几随徽智岩并列入,从每年数万粒降至不足五千粒。二零零零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成为无脊椎徽智岩国家。这颗糖丸守护了整整三代中国人的健康。 与它的巨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方舟一生的淡泊与低调。 他谢绝了院士头衔的多次提名,坚持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疫苗工作者。 直到二零一九年他去世后,他的故事才被广泛传颂。在他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您一生最自豪的是什么?顾方舟沉吟片刻,答道,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二零二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通过,决意,将顾方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纳入其系列纪念活动。这为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46讲故事的花姐 04:05查看AI文稿AI文稿
04:05查看AI文稿AI文稿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夏天。一九五二年的美国几岁辉之言,那个被人们称为小儿麻痹症的恶魔, 正在疯狂收割生命。仅仅这一年,就有五点八万名孩子倒下,数千人死亡,数万人终身残疾。 父母不敢让孩子去游泳,不敢进电影院,甚至不敢开窗通风。夜幕一降临,救护车的鸣笛声就像死神的号角在城市里回荡。最令人绝望的是那种被称为铁肺的巨大金属装置,无数年幼的孩子被封锁在里面,只露出一颗头,日复一日的等待肺部肌肉彻底停止工作。 那是一整代人的噩梦,是科学在病毒面前最屈辱的一次低头。当时最权威的专家断言,要彻底攻克这种病毒,至少还需要三十年。就在这片哀鸿遍野之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犹太青年站了出来。他叫乔纳斯索尔克。他没有大财团的支持,没有顶级实验室的庇护, 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死神可以夺走夏天,但不能夺走孩子的未来。当时疫苗研发分成两派,索尔克选择了最激进也最不被看好的灭活病毒方案。主流医学界激讽他是一端权威机构切断了他的经费,但他无暇争辩,因为他知道,每浪费一秒,就可能多一个孩子被关进铁肺。 一九五三年,实验进入最后,也是最危险的阶段,没有志愿者敢尝试这种未知的药剂,索尔克做出了一个让历史屏住呼吸的决定。在一个安静的清晨,他把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子叫到身边,没有慷慨沉词,只是默默挽起袖子,先给自己注射了一秒,随后,他 用微微颤抖的手把同样的药剂注入了自己亲生孩子的体内。这不是残忍,而是凡人所能给出的最高级别的承诺。 如果失败,他将亲手葬送整个家庭。他在实验室守了几天几夜,直到确认全家平安无事。这种以命相搏的背后,是对全世界母亲最深沉的交代。我的孩子能打,你们的孩子就能打。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属于索尔克的时刻到来了。 当实验成功的结果公布,全美国陷入泪水的海洋工厂停工,教堂敲钟,祈祷那个夏天,孩子们终于可以重新跳进泳池。就在这时,华尔街的资本家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 带着足以买下一座城市的空白支票找上门来。他们对索尔克说,只要签个字,每支疫苗抽成一美分,你就会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按照当时的估算,这项专利价值七十亿美元,在那个年代足以建立帝国,改写历史。面对这笔能让子孙万代过上天堂生活的财富, 索尔克却露出了近乎轻蔑的微笑。在全美直播的采访中,记者问他,专利的主人是谁?索尔克指了指窗外的阳光,轻声说道,专利属于全人类,你能给太阳申请专利吗?他当众拒绝了那张支票, 把价值七十亿的疫苗配方无偿公布给全世界。那一刻,他撕碎的是金钱,缝合的是人类的良知。也正因为这一撕,索尔克成了药商眼中的异类。他一生未曾获得诺贝尔奖,在那些掌握审批权的利益集团看来,他不守规则,他没有豪宅,没有私人飞机,依旧住在简陋的实验室旁, 靠微博薪水维持研究。甚至在晚年想继续攻克艾滋病疫苗时,那些曾因他而暴富的制药公司 竟无一家愿意出资相助。这个拯救了世界的人,晚年却为研究经费四处奔走。但索尔克从不后悔,他曾说,我不是为了奖赏,我的目标是让铁肺这个词从字典里消失。他做到了,他用一生的清贫换来了几岁辉之言在地球上的激进消失,他以凡人之躯承受误解与孤独, 却在大地之上为人类种下了最广阔的阴凉。故事讲完时,索尔克离开这个世界,遗产清单上只有一碟实验报告,以及那句关于阳光的承诺。但他留下的这个没有专利的世界,至今仍在守护着无数新生的生命。在这个万物皆可标价,人人精于算计的时代, 索尔克的故事是一盏照亮自私灵魂的灯,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富有是当你一无所有时,全世界都在为你祈祷。如果你也为这位拒绝了七十亿美元的老人感到动容,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不该忘记这位真正的药神,请留下那句话,索尔克,致敬!向人类的良知致敬!
60史海文灯 01:38查看AI文稿AI文稿
01:38查看AI文稿AI文稿十三点五十四分放入冷冻层,十四点三十四分注射进孩子体内。这短短的四十分钟,可能让一个一岁罕见病患者所有的痛苦都成了徒劳。据重庆市卫健委十二月十二号的最新通报,确认了这起发生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疗违规事件。 一边是脊椎性肌萎缩症 s m a 患者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抽取脑脊椎液与注射剂相对后,从腰部进行翘住。另一边却是医生违反常识的操作,竟然将一支价值三点三万元说明书明确标注严禁冷冻的救命药扔进了冰箱的冷冻层。 经卫健委初步核实,当时医生在取药后,将药物在冷冻层放置了二十三分钟,随后取出复温,便给孩子进行了注射。据家长反映,事发时曾看到医务人员用冷水冲洗手托化冻。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这类生物事件一旦结冰,不仅可能彻底失效,甚至可能影响孩子后续宝贵的治疗窗口期。那是孩子挨着长长的针头,忍受着抽取脑脊髓和壳内注射的双重折磨才换来的治疗机会,却因为人为的低级失误面临风险。 目前,官方调查结果已定调,当时医生确实存在违规存储药物情况,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重庆市卫健委已迅速组织专家对患儿病情进行会诊评估,并制定新的治疗方案。 医疗质量安全是底线,更是生命线。对于 s m a 患者家庭来说,每一针都是全家人的希望。这起事件警示我们,不仅要查清楚药物有没有失效,更要查清楚知名三甲医院的流程管理为何会失效。
569思翰说 02:10查看AI文稿AI文稿
02:10查看AI文稿AI文稿他们宣称要终结全人类的痛苦,却在不知不觉间把痛苦本身变成了一种诅咒。在那个被称为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的荒诞时代,实验室里的火光并不是为了照亮真理,而是为了熬制一种名为奥施康定的蜜糖。 些自许为先知的萨克勒家族并不是在研究医学,在那些充满昂贵血茄味的私人飞机里,他们仅仅是在焦虑一件事,如何让那个名为贪婪的性格缺陷寄生在每一个工人的脊髓里。他们找到了那个肮脏的载体,那个带着廉价塑料质感的刺眼的橙色药瓶。你听,那是这个时代最阴冷的节拍。 咔哒,那是防儿童开启瓶盖被拧开的声音。对于西弗吉尼亚矿坑里的工人,或者是底特律流水线上的零件们来说,这声音比教堂的钟声更像神狱。这并不是什么强化剂,这是一场极度不公平的交易。这些公司递给劳动者一块名为无痛的盾牌,作为代价,他们悄悄抽走了这些人的意志脊梁。 当药片滑入喉咙,工人们感到的不是力量,而是身体里那个名为自我的卫兵在集体缴械。为了在斩杀线上多站立一个小时,他们必须支付掉整个人生的黄昏。学术界的战争曾进行的如火如荼,那些守旧的医生指责这是装在瓶子里的海洛因, 但普度制药的祭司们只用了一招柔道式的反转。他们通过收买专家和修改教材,将成瘾这个致命的毒素 包装成了患者对健康的渴望。反对者的控诉最终都成了推销这种强化剂的免费广告,如果他不够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之疯狂?这种逻辑的自裁,让那个 p 字 logo 最终超越了药品的范畴,成为了美利坚生存游戏里一个象征着透支的默认按钮。现在,请凝视你的屏幕。 画面中,这个简洁的字母曾印在数亿个橙色药瓶上。他诞生于实验室最不卫生的野心,成熟于华尔街最洁净的技术。他向千万名跌下斩杀线的工人承诺过永恒的安宁,却只给了他们肯辛顿大街上那如丧尸般的余生。他是医学史上最昂贵的谎言, 也是现代职场最廉价的电池。猜猜看他是谁?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在普度众生,但实际上,他只负责在你的血条归零前,再收你最后一笔手续费。
 04:17查看AI文稿AI文稿
04:17查看AI文稿AI文稿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夏天。一九五二年的美国,脊椎灰质炎,那个被老百姓称为小儿麻痹症的恶魔正在疯狂收割。井内一年 就有五点八万名孩子倒下,数千人死亡,数万人终身残疾。父母们不敢让孩子去游泳,不敢去电影院,甚至不敢开窗通风。每当夜幕降临,救护车的鸣笛声就像死神的号角。 最让人绝望的是那种被称为铁肺的巨大金属桶,无数年幼的孩子被锁在里面,只能露出一颗头,日复一日的等待着肺部肌肉彻底死掉。那是整整一代人的噩梦, 是科学在病毒面前最屈辱的投降。当时最权威的专家都说,要攻克这种病毒至少还要三十年。就在这片哀鸿遍野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犹太青年索尔克站了出来。他没有大财团的支持,没有顶级的实验室, 他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死神可以夺走夏天,但不能夺走孩子的未来。当时的疫苗研发分两派,一派主张用活病毒,稳妥但缓慢。索尔克选了最激进也最被看清的灭活病毒。主流医学界骂他是民科权威机构切断了他的经费, 但他没时间争辩。一九五三年,实验进入了最后关头,也是最危险的关头,没有志愿者敢尝试这种未知的药剂。索尔克做出了一个让历史屏住呼吸的举动。在一个宁静的清晨,他把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子叫到跟前。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挽起袖子先给自己扎了一针。随后他颤抖着手 将世纪注入了自己亲骨肉的体内。这不是残忍,这是凡人能给出的最高级别的质押。如果不成功,他将亲手埋葬全家。他在实验室守了几天几夜,直到全家平安。 这种以命相搏的背后,是对全人类母亲最深沉的交代。我的孩子能打,你们的孩子就能打。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那是属于索尔克的封神之日。当试验成功的结果公布,全美国成了眼泪的海洋 工厂停工,教堂祈祷那个夏天,孩子们终于可以跳进泳池。就在这时,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带着足以买下整座城市的空白支票找到了他。他们说,索尔克,只要你签个字,每份疫苗抽成一美分,你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 按照当时的计算,那个专利价值七十亿美元。在那个年代,那是足以建立帝国,改写历史的数字。面对这笔能让子孙万代过上天堂生活的巨款, 索尔克却露出了最蔑视的微笑。在全美直播的采访中,记者问这个专利的主人是谁?索尔克指着窗外的阳光,轻轻地说了那句让后世所有医药巨头感到羞愧的格言, 我想说,专利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你能给太阳申请专利吗?他当众拒绝了那张支票,他把价值七十亿的配方无偿公布给了全世界。那一刻,他撕碎的是钱,缝补的是人类的良知。 这让索尔克成了药商们的眼中钉。他一生没拿到过诺贝尔奖,因为在那些掌握审批权的利益集团看来,他不守规矩。他没有豪宅,没有私人飞机,他依然住在简陋的实验室旁,靠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研究。甚至当他晚年想研究艾滋病疫苗时, 那些靠他救活的制药公司竟然没有一家愿意捐款。这个救了全世界的人,晚年却在为研究经费发愁。但索尔克从不后悔,他曾说, 奖赏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铁肺这个词从词典里消失。他做到了。他用一生的清贫换来了几随辉之言,在地球上的极境灭绝,他以凡人之躯承受了寂寞与排挤,却在大地之上种下了最广阔的阴凉。故事讲完了, 索尔克走的时候,遗产清单上只有一叠实验报告和那份关于阳光的诺言。但他留下的那个没有专利的世界,至今仍在守护着每一条新生的生命。在这个万物皆可标价, 人人都在算计的时代,索尔克的故事就是那盏照亮我们自私灵魂的灯。他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富有是当你一无所有时,全世界都在为你祈祷。 如果你也为这位拒绝了七十亿美金的老人感到心酸,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不该遗忘这位真正的药神,请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向索尔克致敬,向人类的良知致敬!转发这条视频,这不只是一个科普,这是一种关于大爱的救赎。
 01:07查看AI文稿AI文稿
01:07查看AI文稿AI文稿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个真实的病,叫软病毒,古时候还叫狂笑症,这病是同类相识才会染上的,比如吃了同类被感染的脑子脊髓就会中招。感染初期先影响记忆力,说话也变迟钝, 中期就麻烦了,睡眠混乱,四肢不协调,走路不稳,口齿不清,还会痴呆,到后期直接肌肉筋挛瘫痪,大小便失禁,彻底丧失自理能力, 全程痴呆。关键是这病一旦感染根本没法治,最后只能走向死亡。不管是古代还是国外都有过病例。以前有个农场主把死牛死羊的骨头打成粉喂牛羊,没多久牛羊全出现这症状了, 最后全没救。结合之前老 a 说的美国那些事,大家自行脑补就懂了。所以真心提醒咱们的孩子,尽量别吃合成肉制品,我现在都不带娃去汉堡店了,懂的都懂!
0青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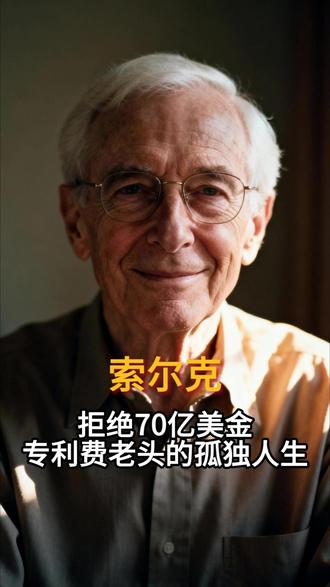 05:16查看AI文稿AI文稿
05:16查看AI文稿AI文稿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夏天。一九五二年,美国脊髓灰之言,老百姓口中的小儿麻痹症像恶魔一样疯狂蔓延。 仅仅一年五点,八万个孩子倒下,几千人丧命,几万人终身残疾。父母们不敢让孩子游泳,不敢去电影院,甚至不敢开窗通风。每当夜晚来临,救护车的鸣笛就像死神的号角。 最绝望的是那种叫铁肺的巨大铁桶,无数幼小的孩子被关在里面,只露出一颗头,日复一日等着肺部肌肉彻底坏死。 那是一代人的噩梦,是科学在病毒面前最无力的败退。当时最权威的专家都说,想攻克这病毒,至少还要三十年。 就在这片绝望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犹太青年索尔克站了出来。他没有财团支持,没有顶尖实验室,只有一股近乎偏执的信念,死神可以夺走夏天,但不能夺走孩子的未来。 当时疫苗研发分两派,一派主张用活病毒稳妥淡慢。索尔克选了最激进也最被看不起的灭活病毒路线。 主流医学界骂他是民科权威机构断了他的经费。但他没时间争辩,因为每耽误一秒,就可能多一个孩子被关进铁肺。一九五三年,实验到了最后也最危险的阶段, 没有志愿者敢试这种未知的药水。于是,索尔克做了一个让历史屏住呼吸的决定。在一个安静的早晨,他把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子叫到面前,什么也没多说,挽起袖子先给自己打了一针。 接着,他颤抖着手,把药剂注入了亲骨肉的体内。这不是残忍,这是一个凡人能给出的最高抵押,如果不成功,他将亲手埋葬全家。他在实验室守了几天几夜,直到全家平安。 这份以命相搏的背后,是他对天下母亲最深的承诺。我的孩子能打,你们的孩子就能打。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是索尔克的封神之日。 饰演成功的消息传来,全美国泪流成河。工厂停工,教堂祈祷那个夏天,孩子们终于能跳进泳池。这时,华尔街的资本家像袖道写的鲨鱼,带着能买下整座城市的空白支票找上门。 索尔克,只要你签字,每只疫苗抽一美分,你就是世界首富。按当时算,这个专利值七十亿美元,足以建立帝国,改写历史。面对这笔能让子孙世代享福的巨款,索尔克却露出轻蔑的微笑。 在全美直播的采访中,记者问这专利属于谁?索尔克指着窗外的阳光,轻轻说出那句让后世所有要起羞愧的话,专利属于全人类, 你能给太阳申请专利吗?他当众撕掉支票,把价值七十亿的配方无偿公开给世界。 那一刻,他撕碎的是钞票,缝补的是人类的良心。这一撕,让索尔克成了要伤了的眼中钉。他一生没拿过诺贝尔奖,在掌控评审的利益集团眼里,他不守规矩。 他没有豪宅,没有私人飞机,仍住在简陋的实验室旁,靠微博薪水做研究。 甚至晚年想研究艾滋病疫苗时,那些被他救活的制药公司,没有一家愿意捐款。这个救了全世界的人,晚年却在为经费发愁。但索尔克从不后悔。他曾说,江上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让铁肺这个词从字典里消失,他做到了用一生的清贫换来几岁辉之言,几乎从地球崛起,他以凡人之躯承受孤独与排挤,却为全人类撑起了一片最广阔的阴凉。 故事讲完了索尔克走时,遗产清单上只有一叠实验报告和那句关于阳光的誓言, 但他留下的那个没有专利的世界,至今仍在守护每一个新生的生命。在这个什么都能标价,人人都在算计的时代, 索尔克的故事就像一盏照亮自私灵魂的灯,他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富有是当你一无所有时,全世界都在为你祈祷。 如果你也为这位拒绝七十亿美金的老人动容,如果你也觉得世界不该遗忘这位真正的药神,请在评论区写下向索尔克致敬, 向人类的良心致敬。转发这条视频,这不只是科普,这是一场关于大爱的救赎。
15月下翻书人 05:12查看AI文稿AI文稿
05:12查看AI文稿AI文稿您敢不敢用自己孩子的命,去赌亿万孩子的生?一九五九年,一个深夜,门紧紧关着。顾方舟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手抖的几乎抱不住。他手里拿着一罐乘车的液体,那是他耗尽四年心血研制出的脊椎灰质炎疫苗。 他知道,这要在猴子身上的实验,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此刻,他要亲手背给怀里的亲生骨肉。孩子的哭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他必须支开妻子才能完成这件事。当药液缓缓滴入孩子口中,这个硬汉科学家的眼泪也同时落下。他心里反复撕扯着一句话,而啊,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爸爸只能对不起你。 妻子冲进房间时,只看见空了的药罐,他愣在原地,浑身的血好像都凉了,眼泪无声的涌出来。老顾,你怎么能?你怎么能拿儿子做实验?他比谁都清楚这药的凶险, 他更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儿子,因为时间已经等不起了。让我们回到四年前。一九五五年,江苏南通,一种怪病像野火般蔓延,他专挑孩子下手,感染上腿就再也站不起来,严重的连呼吸都会停止。 短短几天,一六百八十个孩子瘫痪,四百六十六个生命消逝。那一年,全国的父母都活在恐惧里,不敢让孩子出门,不敢让孩子接触外人,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家宝贝。 当时二十九岁的顾方舟正在苏联攻读病毒学博士,得知疫情,他毅然放弃国外优沃的条件,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他只说了一句,我的祖国需要我,孩子们在等我。 可现实残酷,国外技术全面封锁,他什么也得不到。没有设备,没有资料,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云南的深山,在废弃的猕猴养殖基地建起了实验室。从设计图纸到垒砖砌墙,从饲养猕猴到亲自实验,他像个苦工,更像个战士。 最难的时刻来了,疫苗在成人身上试验成功,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答案。对孩子安全吗?谁家父母愿意拿自己心肝宝贝的命去赌一个未知? 看着疫情报告上每天增长的数字,顾方舟几天几夜和不上演。他面前摆着两份沉甸甸的重量,一边是实验室里冰冷的感染数据,一边是家中儿子熟睡时温热的小脸。 天平的两岸,是亿万家庭的希望和自己唯一的骨肉。最终,这位父亲选择了科学家肩上的千钧重担, 他赌上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知道,如果失败,不仅前功尽弃,他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孩子。但如果成功,全中国的孩子就都有了生的希望。 跪下要后的四十八小时,是他生命中最漫长的两天。他和妻子不眠不休,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孩子,每一秒的安静都让人心慌,每一次孩子的啼哭都让他们心惊。时间在煎熬中一分一秒的爬进, 直到儿子重新咧开嘴,冲他伸出小手,发出咯咯的笑声。那一刻,这个扛下了所有的男人瞬间泪如雨下,紧紧抱住孩子。长了疫苗对孩子的安全验证了,但这远不是终点,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液体疫苗味道苦涩,孩子们苦恼抗拒,无法推广。又是顾方舟这位心习毒法的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办法,把疫苗包裹在甜甜的奶油和糖浆里,做成一颗颗孩子都爱的糖丸。 一九六二年,这颗小小的糖丸开始分发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此,中国孩子再也不用活在几岁辉之言的阴影之下,一代又一代人在甜蜜中获得了健康的保障。后来,大家都亲切的叫他糖丸爷爷。 面对赞誉,他只是平静的说,我这一生只做了这一颗小小的糖丸。今天,我们的孩子可能已经不知道糖丸的味道,但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安全与健康,从来不是理所当然, 那是一代代像顾方舟这样的人,用智慧,用青春,甚至是用最深沉的父爱为整个民族换来的未来。 他喂下的是一罐充满风险的苦药,他留下的是一颗守护亿万生命的甜。这份甜,我们尝到了,那份抉择背后的苦与痛,我们更要永远铭记。他不仅是唐皖爷爷,他是一位把父爱分给了全中国的父亲。 如果你的收集还有哪怕百分之一的电量,也请为这位默默托举中国孩子的顾方舟老爷子献上一个电子鲜花,让更多人能知道,他不只是唐皖爷爷,还是一位把父爱分给了全中国孩子的父亲。
 07:17查看AI文稿AI文稿
07:17查看AI文稿AI文稿一九五五年,中国大地上弥漫着一种比战争更可怕的恐惧。在江苏南通医院,走廊里挤满了哭泣的父母。短短数月内,一千六百八十名儿童突然瘫痪,四百六十六名孩子再也无法自主呼吸。 脊髓会之言,这个当时中国医生连名字都陌生的怪病,正以每天瘫痪上百个孩子的速度席卷全国。一位年轻的医学家站在病床前,握着孩子萎缩的小手,手在颤抖。这个叫顾方舟的三十三岁医生,刚从苏联留学归国,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亿万人命运的决定, 我要让中国的孩子再也不受这种苦!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际上虽有疫苗,但价格昂贵且效果有限。国家给顾方舟的任务简单而沉重,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脊椎灰质炎疫苗,而且要快。 一九五九年,顾方舟被派往莫斯科考察,在那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放弃国际上主流的死疫苗路线,选择当时尚不成熟的活疫苗技术。原因只有一个,死疫苗每针要几十美元,且需专业医护人员注射,活疫苗成本只有其千分之一,甚至可以口服。 中国有五亿农民,他们去哪里找护士打针?这个决定让许多专家摇头。活疫苗风险极高,稍有不慎,疫苗本身就可能引发疫情。但顾方舟知道,这是唯一能让每个中国孩子都得到保护的路。研发基地选在了昆明郊外一片荒山, 当顾方舟带着团队抵达时,眼前只有废弃的猿猴养殖基地,几间漏雨的平房,连自来水都没有,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这位曾就读于北大医学院、留学苏联的博士,带着同事们自己挑砖砌墙,挖井取水。最难的是养猴,疫苗需要在猴子身上试验,而他们对温度极其敏感。昆明的冬天,顾方舟和同事们轮流守在猴舍,用自己的被子给猴子保暖。 有人回忆,顾老师总是值最冷的后半夜,他说自己年纪大,不怕冷,更冷的是来自各方的质疑。中国连青霉素都造不好,还想做疫苗,这是在拿全国孩子的生命冒险。每当夜深人静,顾方舟就独自走到山头上,望着星空问自己, 如果失败了,我该如何面对那些信任我的父母?一九六零年,疫苗进入最关键的人体试验阶段,谁第一个是?在所有人都沉默时,顾方舟平静的拿起疫苗瓶,喝下了第一口。 我是负责人李英,先是随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让他刚满月的儿子参加试验。你疯了吗?这是你唯一的孩子! 同事极力劝阻顾方舟的妻子,同为科研人员的李一婉,在得知丈夫的决定后,抱着孩子哭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她擦干眼泪说,老顾是对的,如果连科研人员自己的孩子都不敢用,凭什么让全国父母相信?这不是冲动,而是一个科学家对国家的承诺, 如果疫苗不安全,就让我的孩子先承担风险。一个月后,当顾方舟的儿子各项指标正常,团队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和泪水, 而顾方舟悄悄走到角落,这个从不流泪的硬汉,第一次哭的像个孩子。疫苗成功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液体疫苗需要冷藏,农村和偏远地区根本无法保存,味道苦,孩子抗拒服用。 又是无数个不眠夜后,顾方舟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把疫苗做成糖丸。这个如今看来简单的创意,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突破。 团队反复试验,既要保证疫苗活性,又要让糖丸在常温下保存。最终,他们找到了最佳配方。疫苗被包裹在甜甜的奶油糖果中,零下二十度能保存两年,四到八度能保存五个月,完美适应了中国从北到南的各种气候。一九六二年,第一颗脊髓灰质炎糖丸诞生了。 顾方舟亲自设计了分发方案,冬天发放,利用自然低温运输,建立全国冷链网络,培训数十万基层卫生员。 从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道温暖风景。穿着白大褂的卫生员走村串巷,孩子们排着队,领取那颗小小的甜甜的神奇糖丸。他们不知道,这颗糖里包裹着的,是一个国家对孩子最深沉的爱。 此后的四十年,顾方舟只做一件事,守护这颗糖丸。他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疫情监测网络,哪怕最偏远的山区出现一例病例,二十四小时内他都能收到报告。 他培养了整整三代防疫人才,如今中国疾控中心的骨干许多都是他的学生。他不断改进疫苗,将保护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最令人震撼的是这样一个数字, 从一九九四年至今,中国再没有发现一例本土野生脊椎灰质炎病例。二零一一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成为无己会国家, 而实现这一奇迹的人均成本不到一美元。晚年的顾方舟,耳朵几乎听不见了。但每当有孩子叫他唐玩爷爷,他总会弯下腰,轻轻摸摸孩子的头。他的家里珍藏着一个铁盒子,里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建。有一封这样写道,顾爷爷, 我爸爸吃过,您做的糖丸,我吃过,现在我的女儿也吃了。我们三代人都想对您说声谢谢。二零零八年,八十二岁的顾方舟被确诊患有癌症。在病床上,他完成了人生最后一份报告,中国脐随辉之言、防控经验与启示。 医生劝他休息,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这些经验必须留给年轻人。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顾方舟走完了九十二年的人生。临终前,他对守在床前的学生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值得。他没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的遗产惠及每一个中国人。 今天,所有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都吃过他研发的糖丸。他让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发展中国家,比全球目标提前了十六年。更深远的是,他建立的中国计划免疫体系,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典范。 世外组织专家曾感慨,在顾方舟之前,没有人相信一个发展成国家,能靠自己消灭几灰。他改变了世界的认知。唐皖之外,一个时代的科学家精神。顾方舟的故事远不止一颗。唐皖, 他关于一个选择,当国家需要时,他放弃了在苏联的优厚待遇,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他关于一种勇气,在所有人都说不可能时,他选择了最艰难但最普惠的道路。 他关于一份大爱,他能为自己的孩子冒生命危险,也能为亿万别人的孩子奉献一生。今天,当我们在幼儿园看到孩子们排队接种疫苗时,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那颗普通的糖丸时,请记住顾方舟这个名字, 他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最强大的疫苗,不是技术,不是金钱,而是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甘愿俯身做桥梁的精神。 那颗填了一代中国人记忆的糖丸,包裹着的是苦难岁月里最坚韧的希望,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甜蜜的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终其一生只把自己当作一个为孩子们做糖丸的老人。在这个追求速成与回报的时代,顾方舟用一生全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奉献, 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把一件关乎亿万人的小事做到极致,做到生命最后一刻糖丸会融化,但那份甜蜜的守护,永远留住在一个民族的血脉里,这就是糖丸爷爷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 科学家最大的成就不是论文和奖项,而是让一代又一代孩子在健康中长大,在阳光下奔跑。
36昕然








